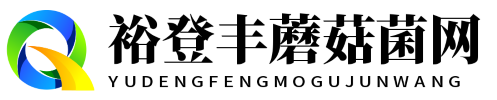中国各地有什么好吃的蘑菇或者说菌类?
中国人又把它称为“白蘑”“口蘑”。作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大宗贸易品,很早以前,蘑菇就被打上了“张家口”这样的地域标签。
广义的蘑菇,是中国人对所有食用真菌的统称。无论是东北的榛蘑、华北的平菇、江浙的香菇、岭南的草菇、滇黔的鸡枞、西域的羊肚菌……它们都能用蘑菇,这个万能的名词来概括。
作为一种食材,蘑菇清晰地指出了中华文明的来处,也见证了这个国家开疆拓土、民族融合的大历史。它是中国人江湖里的儒释道、诗词中的风雅颂、餐桌上的家春秋。
解构蘑菇的底色,要从“菇”的由来说起。在农耕文明眼里,大型真菌是一种笼罩着神秘面纱的食材。它不像瓜果粮食,依靠种子繁衍;也不像蔬菜草木,依靠阳光生长。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没办法种植真菌,也不清楚它们的繁殖生长条件。只有在野外采集中,才能偶尔获得这种饱含氨基酸的鲜美。
浪漫的中国人认为真菌无根无蒂、无体无形,是采纳天地灵气和日月精华而生。顺理成章地,真菌也登上了中国菜里最上品食材的殿堂。《吕氏春秋》里记载:“味之美者,越骆之菌”。先秦时代长江以南的百越之地农业开发程度很低,从那里获取野生真菌,并被千里迢迢送往中原诸侯的餐桌上,可见中国人对真菌的珍视。
这种珍视,也反映在汉字造字中——为了准确描述各类真菌的特点,中国人发明了很多专用字,比如柔软片状的耳类称为“䓴”、长在硬木上的称为“蕈”、长在田里的称为“菌”、带有香味的称为“芝”。到今天,“䓴”和“蕈”依然在山西的晋语和江浙的吴语里有广泛的应用;“菌“在西学东渐之后,被扩展成了一大类生物的统称,包括霉菌、细菌、黏菌等等,但中国人依然为它的本意保留了一个专属的读音:jùn(俊);“芝”成为一个形容词,广泛地比喻各种美好的事物:女子貌美叫“芝颜”,品行高洁叫“芝桂”,气度轩昂叫“芝宇”,行从銮驾华丽叫“芝盖”,而从西域传入的有奇特香味的植物,则被命名为“芝麻”。以小见大、会意类比的汉字,反映了中国饮食的博大精深和食用真菌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菇”,是它们中最特殊的一个。汉以前,中国人的主食除了小麦、稻米、黄米、粟米等之外,还有一种名叫“菰米”的水生粮食。这种植物容易被菰黑粉菌寄生,不再抽穗开花结籽,所以产量一直不能提升。但中国人发现,得病的菰茎会长得肥大而细嫩。人们把它称为“茭郁”,也就是后来的茭白。《尔雅》记载:“邃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东啖之甜滑。”《尔雅》成书于秦汉间,可见当时除了用菰籽作为粮食外,已用茭白为菜。
因为茭白的质地颜色与许多真菌类似,汉始,中国人开始用“菰”指代一部分真菌,并还创造了与之同音、形似的“菇”字。在《玉篇》、《唐韵》等古籍中,多次出现了菰、菇混用的情况。在茭白种植面积广泛的长江中下游,“菇”字的使用尤为普遍。在隋代描述温州永嘉风物的《山蔬谱》中,已经有了“香菌,百姓俗称香菇,有冬春二种,冬菇尤佳”的句子。而“菇”真正战胜䓴、蕈、菌、芝,成为食用真菌的统称,则来自长城以北的另一段传奇。
公元前234年,北方草原上的挛鞮部落,降生了一个男婴。三十年后,长大的男孩带着他的部众们,灭东胡、逐月氏、吞楼烦,甚至南下夺取了肥沃的河套平原,逼迫刚刚从秦末战争泥潭中走出来的汉朝和亲,最终建立了草原上第一个统一帝国:强大的匈奴。汉代的史书里,把他称为“冒顿单于”。
虽然古匈奴语已经散佚湮灭,“冒顿”具体的意思无从知晓,但这位横扫的草原君主,确实对后世的游牧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今天,他名字的词根(mo),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里,依然有“耳熟能详、人尽皆知”的意思。比如,在蒙古语里,人们把草原上随处可见,牧民都喜欢吃的真菌称为(moog)。南宋末年,蒙元入主中原,虽然很多汉学家为南宋的覆灭扼腕叹息,但从更大的历史脉络来看,它只是这个国家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无数次此消彼长、文化融合的片段。大量蒙文化、蒙语被带进了内地,交织、嬗变,最终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或许是为了尊重南宋故地江浙地区的文化传统,又或许是为了翻译得信达雅,蒙语中的moog,被关联到了汉语的“菇”字。还为它专门创造了一个新的汉字“蘑”。融合了游牧语言和农耕文字的“蘑菇”,从此成为了中国人眼中所有食用真菌的统称,它折射了中国二元文明的基本面,也证明了中国人的包容、聪慧和与时俱进。
巧合的是,这次文化大合流,与另一件农业史上的大事发生时间线上的重叠——真菌栽培技术的成熟。事实上,早在初唐时期,就已有南方人“以霉月断树,置深林中,密斫之,蒸成菌”的记载。但季节的限定和杂菌的寄生,限制了人工栽培的进一步发展。南宋年间,丽水庆元县农民吴煜,根据前朝砍树出菇的经验,总结了原木砍花法——以刀痕深浅、大小、位置、方向的不同,控制真菌生长的密度数量,辅以合乎科学的人工管理和加工工序,种出了世界上第一批人工培植的食用真菌。
在西方还在通过驯养猪狗,依靠动物嗅觉寻找野生食用真菌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完成了蘑菇的批量生产,比法国人发现真菌孢子并应用于农业足足早了400年。无疑,这是超越时代的技术进步。更让人惊叹的是,浙南山区百姓种植香菇,至今依然在沿用当时的技术。来自蒙语的“蘑菇”,作为通用名词的大范围流行,与宋元交替时代中国食用菌产量爆发,有着很深的关系。
元以后,随着改土归流的持续推进、满清的入关、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等一系列大事件,包括东北、西北、西南在内的土地被纳入中华版图,越来越多的“蘑菇”走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与经济发达地区依靠栽培获得蘑菇不同,农业基础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会更倾向于采集各种野生蘑菇。在开疆拓土之后的融合过程中,边远地区的各类野生蘑菇,源源不断地作为商品输送到内地,丰富了士子百姓的餐桌,也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在清初的《闲情偶记》中,出现了蘑菇羹、蘑菇面、蘑菇汤;而稍晚的《随园食单》里,蕈、菇两字出现的频率更是多达53次。作为中餐重要的食材,各种各样的蘑菇在清中叶时,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汤菜、炒菜、煨菜和点心的制作中。虽然有误食中毒的风险,但野生菌繁多的种类,提供了多元且复合的滋味,这是人工栽培的蘑菇无法替代的鲜美。即便到了今天,全世界有食用价值的500多种蘑菇里,真正能被人工栽培的,依然不超过50种。
中国的蘑菇文化,不仅仅根植于本土,它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1664年,宋人发明的原木砍花法传到日本,在九州岛东北部,当地人通过原木培植,收获了17公斤干香菇。这是日本最早关于人工栽培食用真菌的记载。对于当时还处在禁肉令时代的日本人来说,食用真菌不是偶尔品尝的鲜美,而是人们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从此以后,日本在蘑菇的人工培植上渐行渐远,走出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1892年,植物学家田中长岭出版《参河香蕈培养图解》,首次阐明了香菇孢子繁殖的原理;1898年,兴农园开始出售香菇菌种,这是东亚地区第一个将真菌孢子商品化的现代化农场;1904年, 三寸种三郎开始“嵌木法”和“菇木汁法”栽培试验,并于十年后普及“嵌木法”种植,这是南宋之后,东亚地区人工栽培真菌的最大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日本还在人工培植蘑菇多样化方面颇有建树,包括猴头菇、金针菇、杏鲍菇在内的,从前并不常见的那些蘑菇,都是由日本率先发明人工培植技术后,才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是的,在中国人拼命发掘野生蘑菇美味的数百年里,日本已经在人工种植上迎头赶超。1970年,日本干菇年产量达到4000吨,一跃成为全球食用菌第一大国。
而当时的中国,蘑菇栽培业不仅落后,而且品种单一。从宋朝的苏轼、高似孙,一直到现当代的王世襄、汪曾祺,中国文人们都以野生蘑菇为尊,对人工栽培的品种,既看不上眼,也不屑于吃。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对蘑菇栽培业的态度。1966年,浙江省给丽水市布置任务,搜集毛主席想吃的新鲜香菇,龙泉泗源乡发动民兵上山寻找,100 多人一天才找到20朵鲜香菇;1979年,亚洲羽毛球赛举行,日本运动员要求以香菇为必备食品,作为全国香菇主产地的丽水庆元,倾全县之力也只能提供10公斤。数百年积贫积弱,由此可见一斑。
但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门被打开,中国蘑菇,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从1978年全国产量不足10万吨,仅占全球总产的5.7%,到2013年已增长到3170万吨,占全球70%。其中,干香菇更成为第一种不经政府政策协调,完全抛弃统购统销,融入市场经济的农产品。
只用了三十多年时间,中国蘑菇全面超越日本,重新登上全球食用菌产量第一大国的宝座。一朵小小菌伞里的千年跌宕与蝶变,折射了中国餐桌对蘑菇始终如一的青睐,又或许隐喻了这个国家愈挫愈勇、风吹又生的民族品质,与我们重塑唐宋、再造盛世的信念。
东北名菜“小鸡炖蘑菇”,不少黑龙江人用的就是元蘑。相比于榛蘑、口蘑,元蘑炖的鸡肉更嫩滑、富含更多胶质,可以说各有擅场。但元蘑最地道的吃法应该是滑炒。搭配快刀抹的鸡脯肉薄片,用蛋清、淀粉抓匀上浆,再与元蘑片一起在旺火热油里炝熟。元蘑爽滑、鸡脯肉嫩滑,二者相得益彰,这是东三省少见的清淡优美、锐利明快的滋味。吃滑炒元蘑最好搭配一壶土气逼人的玉米烧酒,窗外能看见大兴安岭的莽莽森林。这才是原汁原味的东北味道。
红蘑在吉林又被称为“松树伞”,是产在长白山松树林地中的暗红色小型蘑菇。与元蘑相似,它也是小鸡炖蘑菇的重要选择之一。不少吉林人都觉得,所有不用松树伞的小鸡炖蘑菇,都是“”,由此可见红蘑滋味之“正”。
最具吉林本地风味的做法是红蘑土豆片。作为新传入的植物,土豆早在明末期就已传入东北,在冬季漫长苦寒的长白山区,环境适应性超强的土豆一举改变了当地的农耕环境,填饱了无数闯关东的百姓的肚子。而红蘑鲜美的风味,则是土豆最好的搭配和奖赏。红蘑土豆片要用春夏之际收获的红蘑晒干,浓缩凝固季节限定的风味。储藏到秋天土豆收获的时候,再泡发来炒。配菜不宜多,胡萝卜、尖椒、蒜瓣,简简单单清炒后,下水略炖,红蘑的滋味,就会渗入每一片土豆之中。
榛蘑在生物学里被称为“蜜环菌”,顾名思义,就是兼有坚果的香气和微甜的滋味。这种在东北菜里最常被用于炖鸡的蘑菇绝非偶然,它的味道与肉类有天然的契合。当江浙人炖鸡需要加红枣、酱油、糖、味精的时候,辽宁人丢进鸡汤锅里的几枚榛蘑,就能覆盖所有的调味料。
榛蘑炖鸡的配菜和调味料丰简由人,土豆宽粉、葱姜、桂皮香叶,全看心情。最重要的一点是炖煮的时间一定要够久,否则榛蘑的鲜甜就不能彻底析出,并与鸡肉的鲜美融为一体。最好炖到油水分离,浅的鸡汤上已经漂出一层油花,鸡肉吸收了蘑菇的山野清气,蘑菇饱饮了鸡汤的浓香厚味。二者相遇,天造地设的美味。
因为“蘑”来自蒙古语,这个字还影响了内蒙周围的东三省和大北京地区,出产于此的大部分食用真菌都有个“蘑”为结尾的名字。
内蒙古最耳熟能详的特产当然是草原上的口蘑,但事实上,产自大兴安岭西南山麓阿尔山的小黄蘑,才是被内蒙人交口称颂的至鲜之物。
这种产自松林里的小巧蘑菇,带有天然的素,每年夏秋之交,就会大量生长。鲜黄蘑最适宜炒肉片,旺火快炒,飞速出锅,保留原汁,香嫩爽滑。但因为赏味期限短,牧民山民常常将它晒储存;干黄蘑的味道更加浓缩,适宜炖煮菌汤,加在鸡汤里,鲜上加鲜,能得到更丰沛的滋味。
巴楚菇的本名叫胡杨菇,因为生长在新疆叶尔羌河流域的巴楚县而得名。每年的降雨后,伊犁河水泛滥,在当地的胡区,巴楚菇就会从潮湿的树叶中破土而出。
这种伞盖像木耳、伞柄像羊肚菌的蘑菇,肉质非常紧实,当地人常常用羊肉类比它的滋味。巴楚菇最简单的方法是爆炒,按照新疆人喜爱的香辣口味,搭配小米椒、肉丝、洋葱丝一起炒,有天然的烟熏味,极鲜。
被誉为菌中之王的松茸,对生长环境有着近乎苛刻的挑剔,至今仍然无法人工培植。原生态森林、零污染土壤、充沛雨量、强烈光源四大要素,缺一不可。中国中西部的松茸产地很多,但要论最得天独厚的,无疑是林芝。虽然地处雪域高原,但林芝地区却因为雅鲁藏布江的冲刷和青藏高原隆起过程中的褶皱,成为海拔不高的谷地。湿润的环境和充足的日照,让这里草木葳蕤,是藏区的“江南”。
因此,林芝的松茸也被很多人誉为全世界最优质的松茸,尤以巴松措所在的工布江达县所产著名。工布松茸的味道非常好,有特别的浓香,口感如鲍鱼,生吃极其润滑爽口。但最的方法是用竹刀把松茸切成薄片,与草鸡同炖。藏区海拔高,要彻底炖熟需要更长的烹饪时间,无形中完成了西餐中“低温慢煮”的工序,让松茸和鸡肉更加水融。
其实杏鲍菇引入中国的时间很短,2010年前后才在四川培植成功。但四川盆地氤氲潮湿的空气条件,让杏鲍菇有良好的生长环境。到今天,四川已经成为国内杏鲍菇产量最高的省份之一。
杏鲍菇肉质肥厚,质地脆嫩,虽然没有松茸那样的奇鲜,但特别容易吸味。恰好,川菜又是四大菜系里最擅长调味的,由此衍生出的水煮杏鲍菇、麻婆杏鲍菇、宫保杏鲍菇、回锅杏鲍菇、红油菇丁,都是地地道道的川味——可以说,没有肉的时候,几棵杏鲍菇,足以撑起半桌川菜。但杏鲍菇最川式的做法是加入辣酱中,香辣的豆瓣、入味的杏鲍菇、张扬的小米辣、浓香的菜籽油,共同构成了川式菌菇酱的迷人风味。
虽然口蘑不是张家口产的,但张家口为代表的河北中北部、大北京地区饮食中,却绝对不能缺了口蘑。比如在人人爱吃的打卤面里,口蘑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一切辅料。
打卤面的卤子讲究荤素搭配,五花肉煸出油、木耳撕小块、青蒜切碎、蛋液打匀,一起翻炒后加水吊出浓汤,但最最关键的是丢入一些口蘑。它的作用相当于天然味精,能让卤子更浓、更鲜美。最后拌入白水面条充分搅拌,就可以大快朵颐了。对张家口人而言,口蘑并不单纯指野生白蘑菇,事实上,作为草原贸易品集散地,来自蒙古草原的青腿蘑、马莲杆、杏香,都是口蘑家族的成员。所以判断一碗打卤面够不够档次,口蘑种类的丰富与否,是重要的标准。
香菇古代是浙江中部山区的特产,但今天,国内最大的香菇产地却是在河南西峡县。作为秦岭余脉八百里伏牛山的腹地,这里是暖温带与北带分界线,气候温和,特别适宜食用菌生长。1994年,国家提出“南菇北移”战略,缓解南方真菌培植资源枯竭的问题。西峡由此成为共和国最重要的香菇产地。大量香菇的出产,除了做成香菇干四处行销和出口之外,河南人还发明了新吃法——香菇猪肉饺子。
这种耳熟能详的食物,其实历史并不长。香菇作为典型的南方食物,饺子作为典型的北方食物,交集的空间不大。早三十年前,它的名声远不如白菜猪肉饺、三鲜饺、海肠韭菜饺。但“南菇北移”后,香菇来到了速冻水饺产量占全国70%以上的河南。也许是为了合理高效利用本地特产,香菇自然而然被包进饺子里。它为猪肉解腻去腥,提鲜增味的效果很快被人认同,短短几十年后,香菇猪肉,俨然已经成为能与白菜猪肉分庭抗礼的经典饺子口味。
鲁菜是各大菜系中最讲究火候的,简单的油炸,就分出清炸、干炸、软炸、酥炸种种不同的方法来。清炸是不裹面衣直接下锅炸;干炸是拍干粉后入油锅炸到脱水;软炸是打发面糊再裹面衣,炸制后面糊里的空气膨胀,松软可口;酥炸则是在干炸的基础上重新下锅复炸,获得更酥脆掉渣的口感。
对很多南方人来说,平菇是一种几乎没有味道的真菌,只是火锅店菌菇拼盘里凑数的东西,但聪明的鲁菜厨师拿它做软炸鲜蘑和干炸鲜蘑,前者能吃出弹牙,后者能尝到松化。山东和深受鲁菜影响的东北馆子里,都常常拿它作为招牌菜、必点菜出售,这是人人都爱吃的欲罢不能的口味。
蕈油面是苏式汤面里的一种素面,最早流传于常熟地区的寺庙食谱。江南地区寺庙多种松树,雨后的老松上常常长出一些真菌,被人们称为“松树蕈”,滋味鲜美,但保鲜期很短。寺庙里的僧人惜物,采来的松树蕈吃不完舍不得丢弃,就用烧热的菜籽油把松树蕈熬透,可以在阴凉的地方保存一个月以上。
吃的时候就简单了,一箸细面,半碗高汤,连油带蕈浇上去,菜油、酱油、盐、糖包裹着蕈中的精气,既有烈火油烹般的热烈,又有一种亲近自然的妥帖。如果说大油、重色是富庶江南的一种格调,那么素食素面,是人的一种与世无争。
佛跳墙被誉为闽菜之魁。看起来各种食物的大乱炖,但滋味却出人意料的和谐统一。打开造型精致的盅盖,琥珀色的的汤液清澈透明、挂碗不粘。一勺汤入口,一场海陆的盛会就在口中绽放。动物脂肪的甜首当其冲,随后海产的鲜如浪潮席卷而来。鲍鱼的弹牙、鱼翅的Q脆、鸽蛋的香浓……调和这一切的,就是花菇的味道。
花菇其实就是香菇,人工栽培的香菇在南方湿润的冬天长得最快,肉质厚,黑色的顶面会爆开白色的花纹,因此得名。晒干的花菇在水发慢炖之下容易吸味,也会释放极有包容性的鲜美。它将佛跳墙里的各色山海珍味联为一体,怪不得能引得禅心乱动,跳墙来食。
茶树菇,顾名思义,是生长在油茶树枯干上的蘑菇。在油茶生长广泛的浙江南部、江西、福建都有产出。其中,尤以江西广昌县和福建古田县出产的质量最佳。
茶树菇和大部分蘑菇都不同,它肉质单薄,并不肥美。但却具有蘑菇很少见的韧嘴耐嚼的质地,是很好的下酒菜。尤其是干煸之后,还能获得爽脆的口感。恰好,江西的腊肉产量也大,且滋味独特。二者结合,把腊肉切成连肥带瘦的小丁,干锅煸出油脂,再用腊肉油煸炒小米辣椒和茶树菇。烟熏味、菇鲜味、辣椒的刺激味,混合在一起,这是南方潮湿的日子里,拿来配烧酒,是莫大的享受。
草菇起源于广东韶关的南华寺中,清前期就已有人工栽培的文献记载。这种菌柄被包裹在菌伞中的外形奇特的蘑菇,是岭南地区最常见的食用真菌。除了炒菜、煲汤、焗烤之外,广东人甚至还拿它参与酱油的制作过程。“草菇老抽”,让豆类发酵的鲜味和草菇的鲜味、焦糖的甜味融为一体,鲜上加鲜,是几乎所有广东人都喜爱的调味料。
时期,下南洋广东华侨把草菇带到东南亚,继而传播全球,让它成为世界上第三大食用菌。有意思的是,下南洋的过程中,广东华侨还带回了另一些海外的东西,比如咖喱。这种味道浓烈的酱汁,具有很好的包容性,各种蔬菜、肉类都能与之搭配而不突兀。鲜美而略显单薄的草菇,也许就是咖喱的绝配。咖喱粉、水淀勾芡,把整朵的草菇煮熟,最后加入多多的椰汁、多多的淡奶、多多的黄油。味道汹涌,却保存了草菇本来的鲜美。这是广东人即传统、又外向的生动体现。
竹荪其实在西南的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各省都有出产,尤其是高温高湿地区,在竹林中的枯死竹根上,很容易长出竹荪。长长的网状菌裙是它最具辨识度的特点,也正是依靠菌裙,竹荪晒干后就变成了多孔、易于吸取汤汁的蜂窝状结构,煲汤最益。
恰好,广西南部沿海地区,与越南红河三角洲、广东珠江三角洲同属粤文化圈区域,都有煲汤的传统。来自广西北部十万大山的竹荪,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南部,成为竹荪丸子汤、竹荪花胶汤、竹荪干贝汤、竹荪莲藕汤、竹荪排骨汤。但生活在两广地区的客家人,还为竹荪想出了另一种吃法:酿肉。猪肉混入马蹄、葱白,酿进中空的竹荪里,再煎到两面金黄。相比于酿苦瓜、酿青椒、酿茄子等传统客家酿菜,竹荪酿肉,更彰显了客家人因地制宜,又不忘传统的风气。
虽然云贵高原在蘑菇菌子的出产上类似,但两个省的味道却有很大区别,贵州自古缺盐,有着以辣、酸等刺激性“大味”代替盐的传统。云南人习惯于焖饭、煲汤的牛肝菌,到了贵州,不是用辣椒爆炒,就不算正宗的本地滋味。
牛肝菌改刀成片、小米辣和葱姜切末,郫县豆瓣炒出红油后一股脑丢进锅大火爆炒。最后再加生抽、白糖、盐调味,要有烟熏火燎的镬气,才能体现贵州人粗犷耿直的脾气。相比于丰腴绵软的牛肝菌汤,爆炒出来的牛肝菌是脆韧的,特别能下酒。
云南的野生蘑菇是全国最著名、产量最大、种类最多的,原因无它:气候适宜、生物系统繁多完善。但如果非要拿一种蘑菇代表云南,那么非鸡枞莫属。老饕张大千在自己的蘑菇画作上题诗:“南诏鸡嵏北口蘑,三川平把许同科”,南诏就是云南的古称,而嵏是枞的通假字。
鸡枞是少有的集肉质细腻、香味高雅、鲜味浓烈为一体的真菌。而且因为它的生长离不开白蚁巢,长期以来人工培植非常困难,比之松茸,也毫不逊色。云南人吃鸡枞的方法很多,红烧、生煎、油炸、炖汤,闭着眼睛烧都好吃。但最具本地特色的应该是凉拌鸡枞:煮到断生的鸡枞,和大蒜末、花生碎、花椒油、芥末油、糖醋盐、香菜拌在一起,爽脆、清新、滋味丰沛。这是来自彩云之南的,最不容错过的美好。
在西方世界,蘑菇也有广大的市场,是人们日常食谱中的必备元素。但论及吃法,不外乎焗烤、烩浓汤和磨碎了调味。没有一个国家,能如中国这样,把小小蘑菇,演绎成精巧而又恢弘的餐桌谱系。从生物学上来看,不从事光合作用的真菌,是食物链最顶端的生物;但擅长化整为零的特性,又能把它归到食物链的最底端。《庄子》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这既是中国人对时间流逝的思考,也归纳了蘑菇中所包含的,物极必反、九九归一的中国哲学。
其实,只要是自然界自然生长的蘑菇,都很好吃。只是现在除非自己去山上采,否则市面上绝大部分都是人工养殖的了。
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家住过几年,那时候的农村和现在还不一样,是更原始的原生态环境,土坡,柴禾垛,土墙根,枯木头,烂草地…..记得每次下雨后,雨停了半个小时左右,我爸在的话,都会带我去墙角下,土坡边,房前屋后,找雨后刚长出来的蘑菇,白白的,肉肉的,肥厚的,嫩嫩的。采摘一些回去,马上炒了来吃,超级鲜香下饭。是记忆中难得的美味。邻村的姑姑家,村外有的野生树林,树林里,即便不下雨时,也可以去采到生长的蘑菇,采回来吃,也是一样的美味。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非常爱吃蘑菇的原因。然而,现在的蘑菇,大多都没有什么香味了。已经没有记忆中的味道了,所以题主,建议你找一些比较原生态的地方,自己去采一些野生的蘑菇来吃,这才是最好吃的蘑菇。至于什么种类,其实只是口感上略有不同,就好比最好吃的平菇,和最好吃的白菇,炒出来都是很好吃的啊。
“宁负千石粟,不愿负猴头羹”,猴头菇在古时候可是玉盘珍馐,能稍微吃到点边角料,都够吹上一辈子的了。毕竟,既稀有,营养价值又高,还好吃!
现在有了成熟的培育技术,猴头菇的食用也普及了。做法也是千奇百怪,藤椒金汤猴头菇、葱椒翡翠猴头菇……总之,围绕猴头菇,大厨们开发了成百上千种特色吃法,每一种都一顶一的好吃。
关于猴头菇,本夫人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习性”,它们喜欢成对出现。采猴头菇的时候,只要找到了一颗猴头菇,往它头部相对的地方看去,一定能找到另一颗猴头菇。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卖队友”,也可以说是相忘于江湖。
阿魏菇也叫草原牛肝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走寻常路,它就是蘑菇家族里特立独行的酷gai,喜干旱,长在戈壁上。
阿魏菇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跟肉一起炒,无论是羊肉还是猪肉,只要放入阿魏菇一炒,肉香和菌香融合,鲜嫩可口,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
当时,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梗,称鲜牛肝菌为“非典克星”。据说有一段时间闹非典,云南却连疑似病例都没有,坊间传闻是因为常吃鲜牛肝菌的缘故,身体抵抗力强。
鲜牛肝菌自带贵族buff,所到之处定会飘来浓郁的坚果香,有种来自深林旷野的感觉。口感也是鲜嫩爽滑,美味程度如果用语言来表达的话,总会觉得少了点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