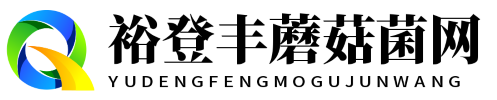周晴烽拍摄菌类成网红拥有50多万粉丝
那天周晴烽拍了鳞钙皮菌的照片发到微博上,这是她后来成为“曳尾菌”这个菌类科普博主身份、拥有54万粉丝的开端。和动物、植物不一样,黏菌是一种微生物,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我拍到的那一丛就有三四个形态,一阵风吹过来,干的速度不一样,它的形态都有很大差别。”对于微小的东西来说,它是无穷无尽的,周晴烽在城市的禁锢和自己的好奇心之间,发现了一个可能的平衡点。

周晴烽利用延时摄影拍摄的发网菌
前几天她在自己公司附近救下了4株兰花。自从发现它们之后,每天上班路上,她都会故意经过那里,多看上几眼,因为城市里野生的兰花很少见。那天是割草机要把草地整理平整,工人们准备连带把兰花也除掉,哪怕它有着特别的淡绿色茎秆和浅粉色的密集花穗,属于肉眼能分辨出来的那种特别。
但城市有它自己运行的一套逻辑,什么东西首先都是有功能性的,没有功能,再少见的兰花也是一种杂草。周晴烽蹲下来选了长得最好看的4株,把兰花举到公司。她住在离公司单程一个半小时的郊区农家院,独门独栋,一年一万多租金,在那里她有一个“密室”,10平方米的房间,起过一场火,墙壁上长了黑毛。
同事们很少知道她的“秘密”。大家更能说出来的是,她在公司做药物研发,已经在上海这个巨型城市生活了5年。她留一头短发,带200度的近,平时穿T恤和冲锋衣,背旧书包,常常一做完实验就下班,罕有参加聚会活动。如果不是因为在公司待得时间够长,她是一个平凡得几乎不会被想起的角色。
2013年刚从中南大学药学专业毕业的时候,周晴烽被老师推荐到中科院工作,存在感更低。“太闲了,每天的工作上午就做完了,大概11点左右,我就下楼摸一趟猫,摸完了以后,就去吃个午饭,吃完午饭呢,回来又摸一遍猫。那时候院子里有好多野猫,不止十几只,它们还经常生娃,生娃了我还要摸小猫,全部挨个摸一遍。”她能做的事情不多,大多是打杂,领导也不管。这给她存下大把的时间和精力,两年的时间里,她把周末能够完成往返的长三角的山都逛了一遍。
那时候周晴烽住在繁华的市中心,但她对城市普遍用来打发时间的方式并不感兴趣,比如游乐场那种玩一次就没意思了,她喜欢丰富的东西。
高中的时候她得到过一本中草药的旧书,上面有用来描述的线描体图画,她经常会拿着图画比对身边看到的植物。高考之前的5月,班级组织去黄山踏青,常年在城市长大的她第一次看到了野生的金银花,她终于找到能和书里对应起来的第一种药材。
那时候小周以为自己喜欢中草药,加上一直看 TVB 关于医生的电视剧,大学选了药学专业。但大一结束,她分子生物学考了六十多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一整个暑假她没有回家,为了能静心学习,找到静下来的方法,还差点去寺庙当居士。
“那段时间就比较挫败,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行。但后来大二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在电脑前面高度集中坐一两个小时,就看植物的信息,发现自己喜欢的是植物,而不是中草药。我当时真的就下了这么一个决心,以后只做喜欢做的事,不做不喜欢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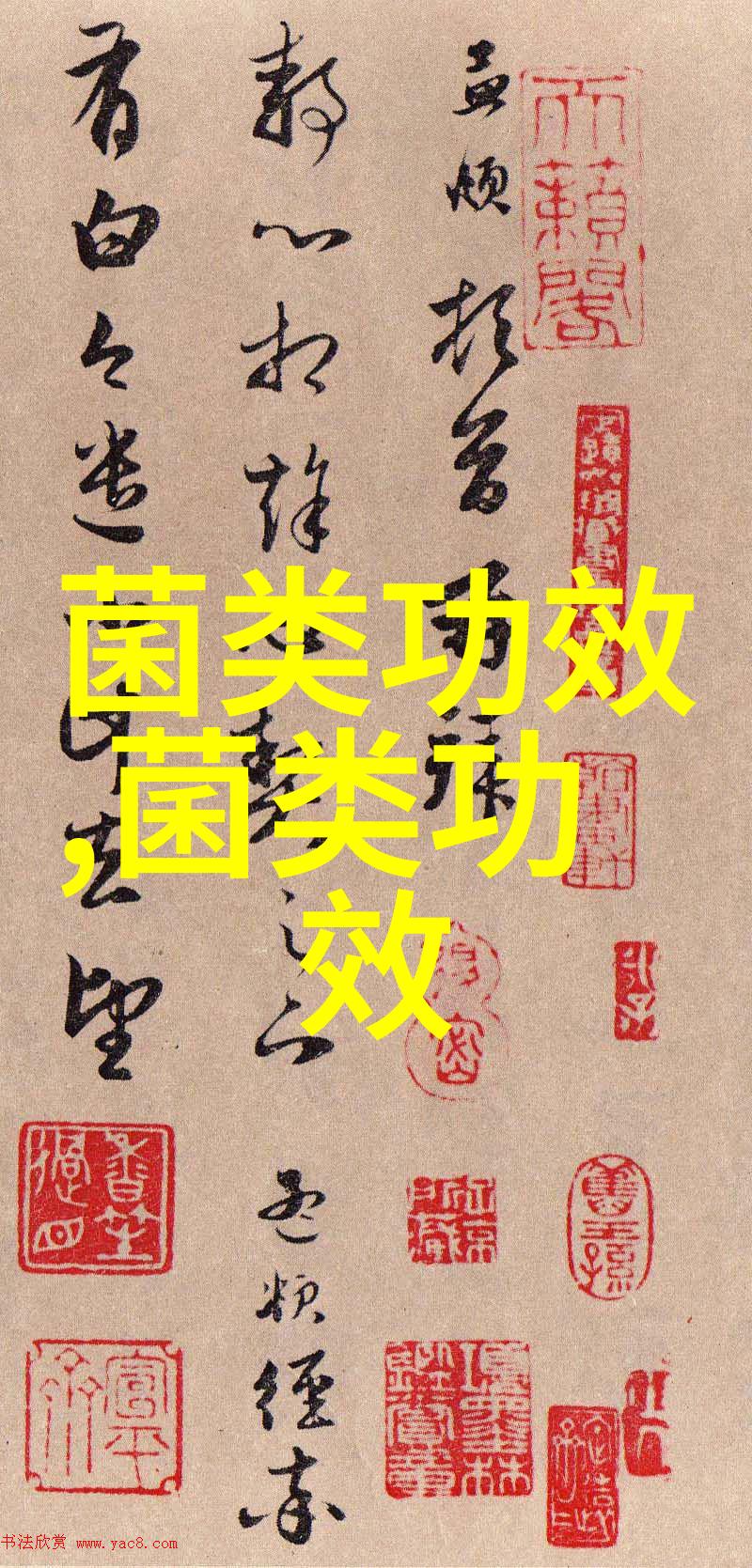
周晴烽从郊外收集马粪,用以养殖菌类周晴烽从郊外收集马粪,用以养殖菌类
在发现自己喜欢植物之后,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学校后面的岳麓山,在那里她认识了一群同样喜欢在山里找新鲜感的朋友。不过她们的年纪偏大,有一次她发了一张登山的合照在朋友圈,评论里问她:“你怎么跟一群妈妈们爬山?”
快毕业的时候,她被推荐去和一群大学生参加华中观鸟营。在湖南屋脊壶瓶山上,同行的人看鸟,周晴烽盯着植物和菌物看。在那里,物种到达了一个她从没见过的丰富程度。“大概海拔高到1500米的时候,我发现走一截,绕一截就发现一条蛇。”在那里,她发现蘑菇菌盖是慢慢摊开的,那是她第一次对菌物产生特别的好奇。
毕业之后,她去了上海,一开始是新鲜的,小区里偶尔能看到刺猬,还有黄鼠狼,但待得越久,越发现它的贫瘠。有一次她去逛徐家汇公园,在整个公园都没见到几只虫子。公园里种的全是麦冬,这种植物不需要怎么打理,非常强势,一种了它,杂草、蘑菇、虫子全都没有了。“你看动物园还知道给动物丰容,堆一点落叶,刨个洞,大城市的人太惨了。”周晴烽对《人物》说。
贫瘠不是唯一困扰她的事情。虽然上海的有趣物种不多,但她只要有时间就出门爬山,上海郊区能走的地方都走过了,浙江、安徽的山也爬遍了,去不了更远,金钱和时间都不允许,她的探索之路就要遇到瓶颈。
2015年5月,有一天晚上,她打着手电筒在中科院宿舍大院里闲逛,上海那些天一直在下雨,她在靠近地面的草本植物叶片上发现了一种比较特别的菌物品种——鳞钙皮菌。平时常见的是鹅绒菌,繁殖期会向四周伸出触角一样生长,但鳞钙皮菌在繁殖期会从白色变成深色,再从深色变成白色,能够爬行。周晴烽把叶片扒开,底下是很厚的一层原质团(黏菌的细胞质),那天她在叶子表面看到的,就是为了繁殖而爬到叶子高处的一部分。


周晴烽拍摄的鳞钙皮菌周晴烽拍摄的鳞钙皮菌
在一天之前,她还在羡慕朋友拍到了黏菌的照片,晚上她就看到了本体,一直看到了夜里十一二点。“周围的狗都被我烦死了,鸟也被我惊飞了,因为我带手电筒到处找来找去的。而且那个鸟它特别搞笑,因为经常被狗凶,叫的时候都是狗‘汪汪’一样的频率。”
那天她拍了鳞钙皮菌的照片发到微博上,这是她后来成为“曳尾菌”这个菌类科普博主身份、拥有54万粉丝的开端。和动物、植物不一样,黏菌是一种微生物,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我拍到的那一丛就有三四个形态,一阵风吹过来,干的速度不一样,它的形态都有很大区别。”她有一个朋友喜欢植物,能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得差不多了,下一步要去非洲才能看到新鲜的。但对于微小的东西来说,它是无穷无尽的,周晴烽在城市的禁锢和自己的好奇心之间,发现了一个可能的平衡点。
和在菌物探索上的顺利相比,周晴烽的工作依然是几乎无意义的重复。在上海的第三年她进入一家私人制药公司,在里面老师带着她学会了药品研发的各种仪器,她也能参与进一些项目当中了。
这种成就感很快被消解,“我刚换到制药这个行业时觉得挺有成就感的,但是去做了就发现,这个成就感不是我能控制的,是整个团队的,团队不行,那我再行也不行。并且里面有很多琐碎是跟法规相关的,没有多少能体现研发精神的东西。做久了发现这其实没什么,就是要绕开各种条条框框,怎么做出一个东西来。”
她放弃了从工作里找满足感,随着时间过去,操作越来越熟练,完成实验几乎成为一种下意识反应,不需要动脑,实验没完就一直做下去。而在她自己挤时间要研究的黏菌上面,小周可以为了拍一个黏菌视频,大晚上来回100多公里去拿菌种,熬夜很久,“为了提神还喝可乐,成本巨大”。
现在的那间“密室”,是她专门为黏菌准备的温室房,用彩钢瓦围起来,冬天的时候放油汀,不小心起火,整个房间都被熏黑了。但还好里面昂贵的相机、相机导轨、录音设备和显微镜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她已经在这上面花了不下10万块。
在2019年引起关注以前,4年里,她为菌物做的几乎一切都无任何现实意义。

周晴烽拍摄的菌类生长周晴烽拍摄的菌类生长
回到长沙一年,离家近,有山,有江,更容易寻找到对于新鲜感的满足。
当时的公司附近有一个几百亩地的小山坡,几乎每天晚上她都上山。“物种超级丰富,那里面不是特别安全,每次去还提心吊胆。”山上最恐怖的不是眼镜蛇,是人。有一次进山,从反方向走过来一个人,天很暗了,没下雨,他却打着一把破伞,吓得周晴烽魂都掉了,“这种人简直就是,简直就是逃犯啊。”那之后,周晴烽一个人上山不打手电。
有一次在岳麓山不小心碰到了以前认识的朋友,周晴烽跟着他去秘密基地,树林里有一块大的平地,里面好多倒木,有很多黏菌。他拿出来相机分享自己在长沙街头行道树上发现的黏菌种类,“行道树有些‘流脓’的木耳,是因为被黏菌吃掉了,照片里黏菌一开始是白白净净的,然后慢慢地变成淡红色、深红色、黑色,最后变成了闪光的五彩斑斓的样子。”周晴烽被惊艳到了,那时她已经有了单反和微距,到处找‘流脓’的木耳,结果在公司附近真的找到了。她用延时摄影把完整的过程拍了下来,是到目前为止她本人最喜欢的视频作品。
要是能一直这样也不错,但长沙的朋友不容易约出来。相比上海来说,长沙更喜欢实在的快乐,一个女生可以为了一块免费蛋糕排一个多小时的队。刚回去的时候,周晴烽像在上海一样,喜欢用打车软件,但在长沙周围人很少用,她也不用了。“就觉得自己是能被环境影响的,我不喜欢这样。”
周晴烽其实不喜欢一个人上山看菌物,她喜欢有同好的人一起。约她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比如有在山下从事金融行业,开劳斯莱斯,一身西服,可一上山就穿牛仔裤、运动鞋的姐姐,也有山下穿白大褂,上山就赤脚的医生。远离城市,大家都“放飞自我”,是平等的。

在树林里观察菌类的周晴烽在树林里观察菌类的周晴烽
虽然离自然更近了,但她并没有远离城市的商业逻辑,小城市的钱比大城市更算钱。时间和工资变少了,有活力的人也稀有,离开上海她觉得孤独,刚到的时候一天哭八次,一年后她又回到了上海。这次租房的时候,她首要的考虑是,要方便建立一个培养黏菌的温室,考虑到房租,她选择了离公司很远的郊区。
“我一直都很不喜欢那种价值观。”周晴烽说。大城市的逻辑向小城市蔓延,国外的逻辑向国内蔓延。一个高中同学留学回国后,曾经找她吃饭,结果对方穿得西装笔挺,周晴烽背着书包在旁边,一路被人盯着看。他以前和周晴烽是一样的,但从国外回来之后天天健身跑步,所谓成功就是必须有钱又优雅。
公司里也是这样,从美国回来的同事说话都很有自信,但是到做项目上总是卡壳。以前待的公司虽然“不打鸡血”,一年能做好几个项目,但如果是国外回来的负责人,一年要换十来个,可能还都做不成。后来公司里的所有人都知道项目很难成功,什么都不会说,能走的人都走了,剩下的是像周晴烽这样老实本分当螺丝钉的。
周晴烽无所谓,她早就认清自己在哪里都只需要当一颗称职的螺丝钉,她的重心被隐秘地折叠在工作日之后。现实越是痛苦的时候,她越容易想起家里的小黑屋,拍摄的灵感越多。
在菌物之前,周晴烽迷恋过观鸟,一个人花两个小时去上海海边举着望远镜看过境的候鸟。在小周看来,那里的鸟不好看,都在冬羽期间,不是繁殖羽。但有些聚在一起观鸟的人,从一些细小的斑点就能区分这些看起来很相似的鸟的种类,“我觉得这有什么好看的,就是都为了找不同去了,好闷啊。”而且观鸟她不喜欢跟着领队,别人看到了然后所有人都去找,让人感觉像在公司里学仪器。
和动植物比起来,人们对菌物的探索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地,到目前为止松茸这样的菌类还都只能通过最原始的采摘完成,更别说是相对冷门的黏菌。“黏菌变化的过程几乎没人拍过,每一个视频都是很重要的记录,没有人做过,才有做的意义嘛,是吧?”这个问题,其实她并不需要任何人回答。
拍摄黏菌照片的并不只有周晴烽一个人,一些微距摄影博主,比如她的朋友南粤荒野一直都有拍,但用延时视频呈现黏菌变化过程的,在国内网络上目前周晴烽是最熟练的人,她对黏菌有特殊的偏爱,有的时候会很直白地叫“菌菌”。
和工作不一样,周晴烽在自己的小黑屋里,一点都不冷静。去年,她在微博上提过好几次抑郁,躺在家里不想动,能够获得的黏菌菌种已经拍得差不多了,想去找新的,家人又不允许她独自上山,自己的培养又总是失败。“太漫长了,久到浪费生命!一个菌种要试验出它的培养条件就要几个月,有的时候做梦都梦到自己养出来了,真的好难受。”她开玩笑说,世界上两大悲剧,万念俱灰和踌躇满志,在研究菌物的很多时间里她都是踌躇满志,着急得坐也不好,站也不好。
有些时候是快乐的。研究出培养条件之后,她会跳起来尖叫,这是浓度极高的瞬间快乐;花至少10个小时进行延时摄影,拍出来发在网络上,被粉丝喜欢,能让她获得持续快乐。甚至是单纯地科普讨论,都透露出掩饰不了的欣喜。
前几年,周晴烽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20多岁的同伴,对方比她还疯狂,山上一条200米的小道,这位女士能兴致盎然地拍半天。“现在我研究出了10多种菌物的培养条件,但是还想做更多,慢慢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最终做一个纪录片,需要很多的素材。”这是周晴烽的最终目标之一。

周晴烽拍摄的菌类生长周晴烽拍摄的菌类生长
但在这条路上,如果能自由且不孤独,是她能想到的最极致的快乐,尽管为此她要一只脚撑着生活,一只脚埋在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