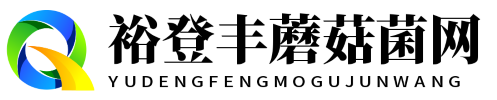农民工子女学校如何“破茧”
在解释赤字原因时,大兴行知学校的理由是:教师工资比其他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平均高一倍;房租过高,年租金30万元;电费比当地居民和公办学校高出近3倍,水费也很高;每年补贴校车18万元;救助学生880人,共减免学费246640元。
李宝元:学校赤字的这些原因,属于有效组织必不可少的经营管理层面的问题,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运营管理和财务管理等一系列领域的基本经营战略和管理策略。
教师工资为什么要比其他农民工子女学校高一倍多,这个标准是怎么确定的?校车补贴是否合理?房租和水电费高,明知是陷阱,为什么还要往里跳?
非营利性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并不是说不算经济账、不搞成本核算、不进行有效的财务管理。这些问题,是由于校长只有“教育”的理想,而欠缺社会企业家基本“经营”理念或策略造成的后果。
不过,即便学校停办申请中提到的原因继续存在,如果所在地政府能在政策实施上公立学校和农民工子女学校一碗水端平,行知学校就不会积累这么多欠款。
我来给大家算一笔账:从2003年起,大兴区以每个孩子每年220元的标准,为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补贴经费。在石景区山区,除了这种公共经费补贴,公办学校每收一名农民工子女,每年还可以获得每人200元的补助。
如果这些补助和补贴也能发给农民工子女学校,行知学校一年就可以获得政府支持504000元。即便每个孩子只享受每年200元的补助,3年下来,行知学校也可以获得72万元补助。
2003年9月1日起施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许多条款要求政府扶持民办教育,如“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的发展”:“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新京报:按理说,像行知学校这样的民办学校,它们承担着的义务教育职能,理应受到政府大力的扶持,但现实为何不容乐观?
信力建:《民办教育促进法》中明文规定了各级政府的义务。但是,它并没有对政府应尽义务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做出明确详尽的列举,有些地方政府因此口惠而实难至。
以大兴行知学校申请停办而言,当地政府就有许多闲置资源,如学校这块物业,为何不拿出来支持民办学校?而事实情况却是,这块物业由辛店村承租给私人房东,私人房东又高价转租给学校。
现在,很多地方的民办教育可以说还处于“三无”状态:无公共政策支持(或说虽有而不到位)、无完善的金融体系提供资金供给、无NGO组织的支持。这造成了民办教育发展步履维艰。
走向“三有”的前提则是,各级政府应提供公共财政政策等支持;完善金融体制,提供融资引资的有效渠道;发挥各种NGO组织的作用。
黄鹤:当初出台《民办教育促进法》时,多数民办学校以贵族式、精英化教育的特点出现。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子女学校大量出现,因为它们完全是义务教育,法律规定应体现为对这类学校的政策扶持。
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据此,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要将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纳入当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范畴;要将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计划,将农民子女就学学校建设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要安排必要的保障经费,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当地水平。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被很好地落实。就目前而言,农民工子女学校很难享得到政策法规的优惠保障,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很难受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比如,大兴行知学校的水电费,当地政府部门完全可以利用行政手段,发挥监管作用。
程方平:对民办教育的不公平待遇,政府主管和督导部门可以出面协调,至少争取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政府主管部门,包括教育、民政、慈善、社会保障、安全、工会、妇联、团组织等应该承认、理解和支持它们所做的贡献,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
新京报:具体到北京,有关文件规定,农民工子女学校要申请到正式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法定代表人必须有北京市户口,有50万元到100万元的注册资金,具备200米跑道的操场等。对这些规定,黄校长怎么看?
黄鹤:对农民工子女学校来说,这种条件过高。这使大量农民工子女学校背上“非法”包袱。现实的做法可以是,除校舍外,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硬件和软件条件按农村义务教育标准执行,教师要有资格证或接受相关培训,校长也要进行资格认证。
杨东平:政府应该从实际出发,把此类学校作为特殊的民办学校对待,以“简易学校”的标准,给它们定性,并提供服务和管理。
北京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大多财力薄弱,办学条件极其简陋,这样的现实,让许多人对农民工子女学校是否能承担起义务教育职能缺乏信心,这也是近年来不断传出农民工子女学校被关闭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农民工子女学校这样一种“低投入”的模式,最终能办出“好教育”吗?
黄鹤:我们的办学模式定位是“非营利性、公益性”,代表着农民工子女学校未来发展的方向,是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学校。教育公平不仅是农民工子女有学上,更主要是教育标准的公平。农民工子女也应该享受合格的、标准的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源,而其中,教师素质是根本保证。因此,行知学校给定的教师工资较高。
黄鹤:我们是“非营利性、公益性”的,和营利性的学校不能比。如果我也是营利性办学,按现在招生规模,一年净赚20万元不成问题。
杨东平:农民工子女学校按非营利模式运行,很有价值和创新意义。但是,如果说是由于非营利、公益性而导致破产,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
东城区百年职校也是此定位,国外的私立学校基本都定位为非营性质。非营利机构也有经营之道,包括筹资能力、成本控制等。
程方平:杨东平说得很有道理,公益也需要资本支撑,没有经费,一切将化为乌有。因此,需要政府的理解和帮助。
其实,资助标准可以协商,对政府部门来说,这是在解决问题同时规避政府风险的可选方案。比如,对黄鹤提出的每个农民工学校的孩子每人补助200元的问题,大兴区教委就可以研究考虑。
新京报:行知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外出参加活动,像参观长城、博物馆等,而每次学校都要贴钱。黄校长,你觉得这样做,值吗?
程方平:我觉得,是否受到好的教育,标准并不在花钱多少,用钢琴培养的音乐素质,用笛子、二胡也能。在没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学生可以通过剪报办自己的“博物馆”,如果参照条件好的学校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必然走入死胡同。
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孩子来说,从熟悉的农村环境来到城市的学校,就如打开了一扇别样的窗。这里有与他成长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积淀,对他来说,一定会有逐渐适应的过程。
很多人误认为,城市中的教育内容一定优越。其实,不同的土壤里会有不同的教育内容,农村孩子对自然的天然感悟,对土地厚重文化的敏感。这些与参观博物馆得到的知识相比,并不逊色。
苏雨桐:对。如果行知学校能更“实际”一些,其实可以省下不少费用。而教育教学效果,说不定还会更好。
这个学校从创立到现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波折,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下才挺了过来,最终获得了合法的办学资格。面对行知学校身陷困境,人们关心的问题是,行知学校如何才能度过眼前的危机?如何才能让这样的危机在行知,以及在所有农民工子女学校不再重演?
程方平:的确如此。从行知学校的情况看,如果不理顺一些关系,不彻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比如适当降低较高的房租、获得适度的财政补贴、在办学中享受政策合理的优惠等,它也许会在短时间内暂时摆脱困境,但最终将会在财务危机中越陷越深。
新京报:如果把现在的行知学校,比喻为一只困在茧中的蝴蝶,在如今的情况下,它怎样才能破茧而出,化蝶轻飞?对这道难题,该怎么求解?
信力建:要给这道难题求解,我觉得,有必要结合社会实际,考虑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将扶持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措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尽可能将原则化的内容具体化,以加强可操作性。
新京报:黄鹤正在四处“化缘”,虽然化到了一些钱,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就眼下而言,行知学校路在何方?
黄鹤:我正在办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务公司和培训中心,这可以作为学校稳定的经济来源,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我的确需要努力成为社会企业家,而不仅仅是做教育家。
李宝元:“化缘”的确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短期内,学校可以靠媒体力量,引来慈善捐助度过难关;但长期来看,必须在完善组织运营模式和规范管理机制方面下工夫。
程方平:黄校长要理一理几个最基本的关系:从包括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儿童保障法等相关法规中,寻求支持依据;审视学校的发展定位和战略战术是否正确,如何更准确、更科学地确定学校的效率目标和特色;对资源、管理、经营等,全部争取社会支持理解的做法是否得当、有效和可持续。[作者:时事访谈员曹保印]